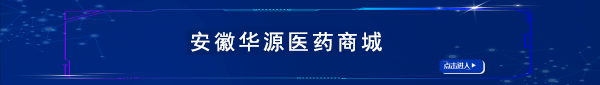“深圳埃格林医药成立于2019年,是由5位前FDA的审评官员与跨国药企的科学家组成。我们这些人都有着5-10年的跨国药企工作经验。我们在专业上也是互补的。我们既有药理/毒理专家,也有临床专家。而在化学和质量控制方面(CMC),我们有着从小分子、大分子,到细胞治疗工艺等各领域的专业经验。专业互补性成就了这家公司的高速成长和发展。”日前,在由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医药创新和投资大会上,中国药促会国际创新药物监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埃格林医药董事长杜涛说。

这些专业背景也使埃格林在选择可开发药品上拥有独到的优势。
“比如埃格林既关注‘有迫切临床需求’的候选药物,也关注那些比较容易开发的‘低垂果实’。大家曾经认为现代医药工业中易于研发的‘低垂果实’已经很难寻找。但是随着人的生命延长,很多曾经不太被关注的人类疾患越来越令人烦恼了。例如,我们所开发和用于治疗眼底干性黄斑病变的候选药物 EG301。人类的眼底干性黄斑病变一般发生在50岁之后,当人的寿命只有60岁的时候,这种疾病的对人类的困扰并不大。但当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超过75岁时,我们就不再能容忍干性黄斑病变造成的老眼昏花甚至是失明。而这个医药研发领域新出现的‘低垂果实’就这样被我们捕捉到。”杜涛说。
埃格林成立三年半共有10条管线中有5条管线进入核心临床。
“我们确确实实是一个追求研发效率的公司。而提高效率的方法一是来自临床适应症的选择;二是来埃格林3年前就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杜涛说。
在杜涛看来,如果一个药品在上市时其专利期不足5年,那这个药品的研发费用基本上无法收回。这会导致医药工业最后变成一个无利可图、资本不愿触碰的行业。这时需要AI技术的介入来破解困境,当然AI技术以及基因组学等与AI制药相关的学科不是今天才产生的,但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一直没有大规模应用和推广,一是需求不高,再就是今天的算法算力的成熟度及数据的规模和可用性是过去不可比拟的。如今,大家可以看到ChatGPT在全球广泛使用,虽说现阶段ChatGPT还不能对创新医药的临床试验起到直接帮助作用,但对于医药研发人员来说,ChatGPT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助手,它具有很强的信息性和逻辑性。因此,对于医药研发人员来说,ChatGPT在信息搜集方面会有很大帮助。
杜涛指出,AI不能直接生产药物,但可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支持与赋能。其中AI技术对药物研发的赋能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端的靶点/分子发现阶段、中间的医药生物学阶段和后端的临床阶段。目前,国内已七十多家AI医药企业,大多集中于前端的靶点/分子阶段,使这部分赛道变得十分拥挤。但事实上,后端的临床阶段才是医药研发最耗费时间和成本的阶段,也是监管最为严格的阶段。通过AI技术的应用,能加速药品的临床试验速度,压缩临床研究的周期,降低临床失败的风险,所能获得经济效益将会更大。正因如此,埃格林做为一家行业领先的AI医药企业,利用自身在临床和监管法规方面的优势,重点选择后端临床阶段做为AI赋能的发力点。